
汪曾祺:读杂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诞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说。但隔了三十年往回看,作家何大草发现,“还能读的,似乎没有几个。汪曾祺先生是其中之一。”汪曾祺1980年发表《受戒》时,已经60岁了。从那时起,他的小说创作贯穿了整个80年代,其作品放到今天,“以挑剔的眼光看,多数仍算精品,个别可列为神品,耐得摩挲、赏玩,意味颇长。这是一个奇迹。”
这也让何大草对文学的秘密感到敬畏:阅读并不是以量可以绝对取胜,关键要形成读书的独特品味。据汪曾祺的儿女回忆,他的藏书“实在是可怜”。《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恩师沈从文的书也只有一本1957年出版的小说选集。家里也没有废名、阿索林的书。倒是契诃夫全集有一套。那么他是否借书读呢?儿女说,他60岁后,也就是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生涯后,“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何大草体悟看来,“汪先生是才子,才气大于学问。他也并不长于虚构。福克纳说:“做一个好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汪先生的长项,就是观察和经验。他的小说,有平静美,包含着情趣和意味。这意味,就是文人味。文人不完全等于文化人。文人味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天资和悟性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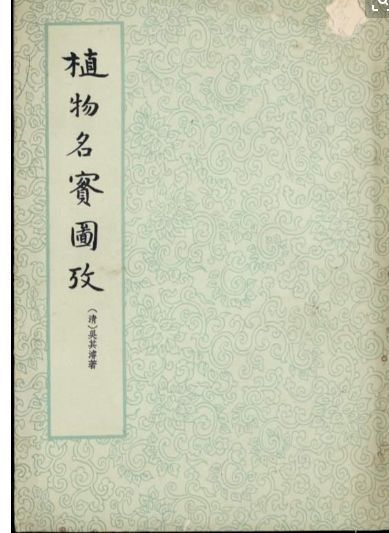
汪曾祺不是藏书狂徒,但他的“阅读”却是有深厚根基和趣味纯正而广阔的。汪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幼年的积淀。他说自己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他所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他喜欢归有光,认为其“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说郑板桥诗文中蔼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动。小学、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高中时还买过一部词学丛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
除了幼年时的家传、中学时代的熏习,青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楚辞课,朱自清先生的宋词,唐兰的“词选”,王力先生的“诗法”课,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的浇灌。另外,还有左传、史记、杜诗诸课,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说《陶庵梦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对外国文学作品,汪曾祺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在文章中他说“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但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
曾经有个青年问汪曾祺:“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汪曾祺在一篇名为《谈读杂书》的文章中说,自己“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看,《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差一点,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我也爱读书论、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宋提刑洗冤录》,这是讲验尸的。有些书本身内容就很庞杂,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了。”《岭表录异》是唐人刘恂所撰,记述岭南异物异事的地理杂记,《岭外代答》是宋代地理名著。汪曾祺认为这类杂书“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而且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他说自己从吴其浚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





评论 0
还没有添加任何评论,快去APP中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