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阎安
/人物简介/
阎安,1965年8月生于陕北乡村。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诗歌委员会主任,文学期刊《延河》主编。2014年以诗集《整理石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已出版《整理石头》《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乌鸦掠过老城上空》《玩具城》《蓝孩子的七个夏天》《无头者的峡谷》《时间患者》《鱼王》《自然主义者的庄园》等多部著作。有部分作品被译成俄语、英语、日语、韩语,在国外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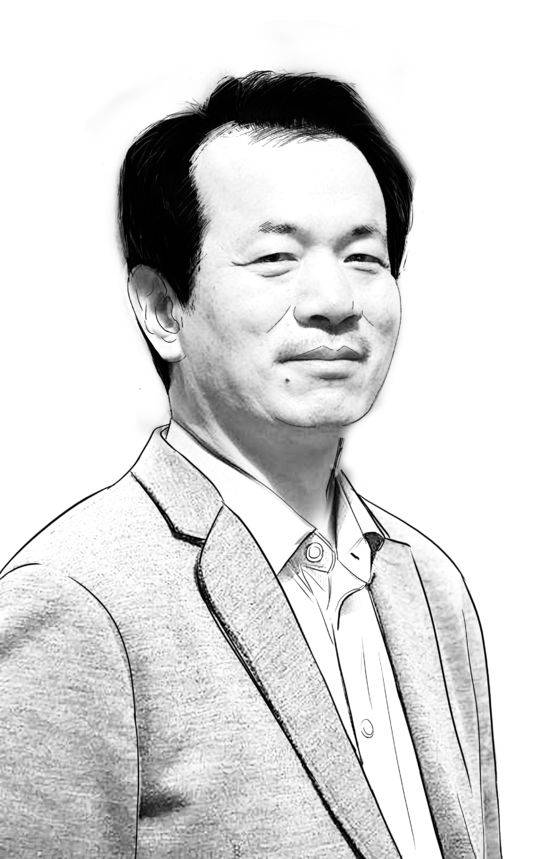
阎安 罗乐/绘
相信读书能把世界变轻,或者通过读书能获得一种把世界变轻的通灵术,然后世界改变了其原有的属性,变得无所不能,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逃脱厄运,化险为夷。
我说的是我爷爷这个人,这个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发起火来不但让家里人,也让全村人毛骨悚然的老兵痞,这个从未读过一天书的人对读书的某种信念,和他教诲子孙后代时那种装模作样,冒充高深的策略。他说别看咱们这个连牛都回不转身子的窄沟旮旯,古时候可出过一个上通天文、下得地理的读书人,他叫热良浩。爷爷大概是当年当兵期间听什么人讲过《三字经》,把“若梁灏”一句囫囵吞枣地误解为一个人名,而“热良浩”这三个字,是我一个上过两年冬学的叔叔,为印证我的追问稀里糊涂写在纸上给我交差的。
我爷爷在我小时候总是反复讲热良浩的故事,但他始终说不清这个读书人具体生活在哪个时代,总是说古代,古时候。有一次,或者好多次,当我固执地质疑和追问热良浩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逼迫爷爷要说出这个才算事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把正好端在手里吃饭的饭碗摔碎在地上,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咆哮道,说古人古事是教你明道理呢,不是跟你闲磕牙呢,三岁的时候看老来,一看你这小兔崽子将来肯定不是个出虱子的跳蚤。我前面说过,我爷爷年轻时当过十五年兵,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过恶仗带过杂兵,杀过好多人,为人霸道,不喜欢别人违拗他,哪怕是在小事上。有好多次,我们就这样弄得不欢而散。
现在想来,我只是想在那个没有多少书可读的时代,想从热良浩的故事中挖出更多的细节。这个故事令我着迷,而细节是故事的灵魂,只有细节才能让我有更多的依据一边望着头顶深渊似的天空发呆,一边想入非非。
我爷爷说,古时候的热良浩,一辈子喜好读书,蓬头垢面,不搭理别人,八十三岁才考中状元,榜书下来的时候,他几乎已老瘫在自家的炕头上了,连走出村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对于不久于人世的热良浩来说,朝廷榜书只是给他多增了一件光芒万丈的陪葬品。热良浩一生最大的壮举,就是有一年,村子里的古树上突然飞来大门扇那么大的一只灰色大龟,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整个村庄,村民们发现,大龟明明就落在树梢上,但它却那么轻,连一片树叶都不能压弯,确切地说,简直就好像没落到树上,而是落到空气中一样。这样一来,大家由不得都感到害怕起来,马上有一种恐惧感开始在全村弥漫,都觉得可能是有一种灭顶之灾就要降临村庄了。这时,有人想起了热良浩,觉得他读书多,应该请他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说这热良浩听了究竟,不急不慌,用合拢的扇骨撩起门帘,探出半个身子,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手搭凉棚只朝树上一望,说了句“千年龟,轻如灰”就转身回房去了。这一句话,把快要压爆全村人心脏的巨石轰隆隆掀飞了,整个村子顿时卸去致命的重负,大家都放心释然了。从此以后,村子果真幸免于难,而且兴旺发达,生生不息。
这个故事始终再未提及接下来这只巨大神龟的去向。对于村里大多数人来说,故事讲到这里,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独独对我来说,事情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我迫切地想知道故事接下来的发展:那只树上的神龟最后去了哪里,它是怎么离开我们村里的。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费了很多周折。我上面说我爷爷是一个阴冷霸道的人,事实上相比而言他的另外一面是他极其敏感,一个时不时夸口在战场上能根据子弹摩擦空气的声音而判断子弹飞来的速度、方向和距离的人,他有一种近乎病态而刻骨铭心的警觉心理,这成为我决心要从他那儿打听出神龟下落的最大障碍。我爷爷只有在高兴的时候才会偶尔讲到热良浩的故事,但他的某种深沉和善变使他很少有高兴的时候,即使他有了高兴的时候,只要我在场,他就会话到嘴边再收回去,绝口不提热良浩的事情。我记得有好多次,试图解开答案的我,极尽努力地做出讨好妥协的样子和爷爷套近乎,都被他一眼识破,他用锐利的目光和表情盯着我看,令我浑身不自在,这时他会抓住机会转身离去,用他那充满傲慢和粗疏态度的背影,把我一个人灰溜溜地扔在一边。
有一度时期,我下定决心自己寻找答案。我先是在村子里找树,我甚至想要找到那棵热良浩活着的时候就长在村子里的树,体会和想象神龟如何以羽毛之轻降临树顶,又如何以扶风之轻离开深渊似地陷在细窄峡谷深处的村庄里的情景,但是村子里没有一棵树。我走出村子在村外的许多山坡上找,那些山坡上也没有一棵树,甚至连草也没有多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北方偏远乡村还没有来得及计划生育,每家每户都稀里糊涂地生了一大堆孩子,农村人口暴涨,当时又没有煤炭之类的现代化燃料,农民烧火做饭养家糊口只能依靠砍树砍柴禾来解决。人们用一种近乎逃命的疯狂状态,挖地三尺地到处搜刮柴禾,草要连根挖,树要连根刨,先是挖光了沟里和山上野生的树和草,紧接着又不惜冒着身陷囹圄的危险,盗伐生产队所剩无几的树木,结果是很多地方地皮都刮光了。那是一个寸草不生、寸树不长光秃秃地荒凉而凄惨的年代,那是一个孩子们上山打柴到头来一无所获只好空手回家因而屡遭父亲毒打的年代。我正是在这样的年代,在我们的村子里,不合时宜而又异想天开地开始了对一棵树的寻找。
由于长时间地找不到树,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魂不守舍、忧心忡忡的人。但是有一次,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我听村子里一个白胡子比山羊胡子长得好不了多少的老头说,村子里还有唯一的一棵树,长在村子里最高的一座山的山顶上,那座山叫顶天山,那棵树仿佛长在天上。我后来果然在村外一座比较高但终归还算平缓的山上,望到了那座天上的山和那棵顶入天空的孤零零的树。我大概足足做了一年时间的准备和计划,我要攀登顶天山,在顶天山上去看那棵树。真实的情况是,要上到那座山的山顶上,必须连续绕过多座巨大而险峻的悬崖,登山就是登天,甚至比登天还难。但是在那年夏季快到麦收时节的某一天正午,我还是一个人偷偷地走出村庄,不自量力地开始独自一人攀登顶天山,当时我要看到那棵树的愿望是那么强烈,简直已经鬼迷心窍。那年我10岁刚刚出头,身单力薄,这个样子当然不可能登上顶天山。事实上那天我上到顶天山半山不久后就迷路了,在试图穿越一块麦地寻求捷径时,我不幸迷失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麦浪深处。那年的麦子长得凶,似乎要高出我头顶很多,我进入麦地就好像陷入了丛林之中,立即呼吸短促,晕头转向。我在麦地深处像一个溺水者在深渊里挣扎,不停地乱扑腾,在一种无法言喻的孤独、绝望、恐惧中愈陷愈深,夜色降临时,我的体力耗尽,浑身就像中了毒似地渐渐陷入麻木。意识到自己就要死在麦地之中,我无声地独自抽泣了很长时间,然后由于极度疲倦和悲哀,慢慢失去了知觉,进入了昏昏沉沉的梦中。我梦见我来到古时候热良浩读书的院子里,那棵在故事中落过巨大神龟的树还在,但树上的神龟已不见了踪影,我想跳起来,跳得像树梢一样高,然后看看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跳了几次,再一次往高跳时,变成了一块云,飞上了树顶。作为一片云,我看到树顶上一无所有,就决定离开树飞向山顶,然后飞向远方。但是刚刚飞到能望见山顶的半空中,我感到全身不明原因地沉重起来,开始向下坠落,而且一阵比一阵更沉重,一阵比一阵坠落得更快,等到完全坠落到峡谷里后,我变成了一块石头,并最终丧失了知觉。
我已不想啰里啰嗦的把这件事情再往下叙述了。只说等我醒来之时,已是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感到自己浑身渺小,虚浮如一块揉皱的纸团,蜷曲在一堆被褥当中,而我爷爷如同一个传说中守护宝藏的巨人,背操双手,一动不动地守护在我跟前。我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我爷爷说,憨孙子呀,爷爷也不知道那神龟到底去了哪里,你若想知道,你就好好读书,等你读的书比热良浩都多了,自然就知道了呀!我后来才了解到,那天我的出走简直成了惊动四邻八乡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我那威震乡里的爷爷为了找到我,动员了周围几个村子几乎所有的青壮劳力,举着火把,鸣枪放炮,遍寻四野,把我们村里的山山洼洼一寸不剩地折腾了大半夜,终于在鸡叫天明时找到了我。
如我爷爷所愿,我后来成了我们村子里继热良浩之后又一个读书人,或者按我爷爷向乡邻夸耀的那样,我实际上成了一个比热良浩更有出息的读书人。我永远记得我上大学离开村子的那一天,我爷爷在村道上送我,我在前,爷爷在后,全村男女老少也黑压压地站在路边参与道别,我爷爷老腰高昂,趾高气扬,一边吼叫一样地大声咳嗽,一边带理不理、志得意满地大声回应各种问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爷爷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异常谦卑温和,简直都有了一种讨好和巴结我的味道,临别时他特别嘱咐:你先去好好读书,以后我有大事给你安顿。我爷爷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只是稍稍感到意外,但并没有太多在意。多少年来,我对我爷爷在很多事情上总是半信半疑,我当然不得不承认他是经历过生死、见过世面的人,但他对人对事的粗暴傲慢和反复无常又总是让我充满敌意,很多年中,我们爷孙为此难成兄弟。但是这一回我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对我的爷爷只能另眼相看,而且因为自己的错误是如此渺小浅薄,我将为此终生抱憾。
我爷爷是在我上大学四年级快要大学毕业时突然病重的,他感到山倒河枯,自己就要寿终正寝,但是闭了几次眼,后来又像梦醒似地睁开了眼,迟迟咽不了气。他给家里人说,发电报给我的大学生孙子叫他回来吧,我有事情要给他安顿。路途迢迢,我在路上周折了七天才回到了村子,我爷爷就上口气不接下口气地等了七天。等我赶到爷爷跟前,他已经只能大口大口送死气了,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再晚回来一天,我就等不上你了。
我爷爷给我安顿说,他在北方沙漠地带打仗时,一共杀死过十七个人,其中九个有名有姓,八个无名无姓,这些人都死在无名的旷野上,无家可归,每天夜里都来敲门打窗,惹是生非。我爷爷说,你是个读书人,你裁上十七个纸条,九个纸条写上那九个人的姓名,八个纸条上分别画上三个圆圈代表那八个人,去北方的沙漠上堆上十七个土堆,把十七个纸条分别压在十七个土堆上,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孙子,你是代表我来安顿他们。我爷爷说,你安顿了他们就好了,我不想去那里以后和这些人继续惹怨斗仇,我想从此过个太平心安的日子。
我爷爷接下来还给我安顿说,他在南方平原上打仗的时候,是个机枪手,到底打死多少人他不知道,算起应该有几百上千人,现在这些人都在南方大平原的无名万人坑里埋着,一到夜里,这些人的尸体就堆山似地压在他的身上,压得他一口气都喘不过来,任他怎么求饶都不放过他。我爷爷说,你是个读书人,你裁上一万张纸条,每张纸条上画三个圆圈代表一个死者,然后去南方的大平原上堆一个大土堆,把一万张纸条都压在大土堆上,焚香颂祷,让那一万具尸体随着一万张纸条飘向空中,从此还他一个轻松宽敞。
我爷爷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读了这么多得书,比热良浩读的书多得多了,现在你一定知道了村子里那只压不弯树梢的神龟到底去了哪里。这最后一句话,我爷爷是叫着我的小名说的,一边说一边禁不住老泪纵横。说完之后,差不多连一个字的间隔都不到,他就嘴一张,腿一蹬,眼一闭,呼呼噜噜痛痛快快地咽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口气,然后几乎在几秒之中他那告别生命的抽搐就迅速恢复了平静,仿佛永远睡着了一般,这时他看上去和一个终生平和的人毫无两样。
我爷爷平生最后说给我的一句话,让我的悲伤五雷轰顶,也让我的悲伤平静而克制,使得我对爷爷的去世表现出一个胜过热良浩的读书人的特有的风度。我大概在一个角落里低低地哭泣了很长时间,然后我用更长的时间保持沉默,因为一种更甚于悲伤的巨大的愧疚。事实上在以后很多年中,甚至一直到今天,这种愧疚像息壤一样一直持续增长,或者也可以说在持续发酵,正是在这一增长和发酵交替进行的过程中,我才渐渐明白,其实当年我爷爷所讲的热良浩的故事中,那只巨大的神龟既存在也不存在,你明白了它就存在,你不明白了它就不存在,任何故事,如果你很狭隘地去计较的话,它一定有结局,但如果你很宽阔地去领悟的话,它一定不意味着某种结局。毫无疑问,既然被读书人热良浩判定的神龟已经那么轻灵,那么神秘,世界上没有它到不了的地方,那么世界上所有宽阔的地方和所有狭隘的地方都不能限制和影响它,所以人们,包括这个故事本身,已完全没有必要替它操心什么了。
很多年又过去了,在我爷爷变成山上的土堆以后,我们村子里的很多人又相继变成了山上的土堆,如今连我们的村子也已经不存在了,但当年我爷爷不厌其烦地讲述的这个故事,这个名叫热良浩的人的故事,这个我们村子里的读书人的故事,却一直令我沉迷不已。我认为事实上这个故事是在探讨人如何像一星之光的恒星那样永生的问题,而且给出了一个直接的隐形性的答案,那就是设法不断地去掉自身的累赘和重量,把世界从内部变轻,轻的就好像不再存在时,它就会自然超越生命和存在犹如包袱般的局限,就能随心所欲地一直走下去,走到最远的地方,而不至于到时候就破碎了,消散了。世界的本质就是无休无止、宽阔无边犹如虚无般的轻,驾轻才可驭重,从而无所不能。
现在,在我确信并确知我们的村子已经不存在以后,我心苍凉,但并不悲哀,因为我相信这个故事还在另外的村子里流传。即使到头来那些另外的村子一个个都荒废了,没人生活了,没有人对人讲故事了,村子本身也会对着废墟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而风会把这个故事带向更加不可思议的远方,甚至能带向恒星和被恒星充斥的茫茫无边的宇宙,让它在更远的更不着边际的地方生根发芽。





评论 1
北海之滨 2019-08-03
好的呀!